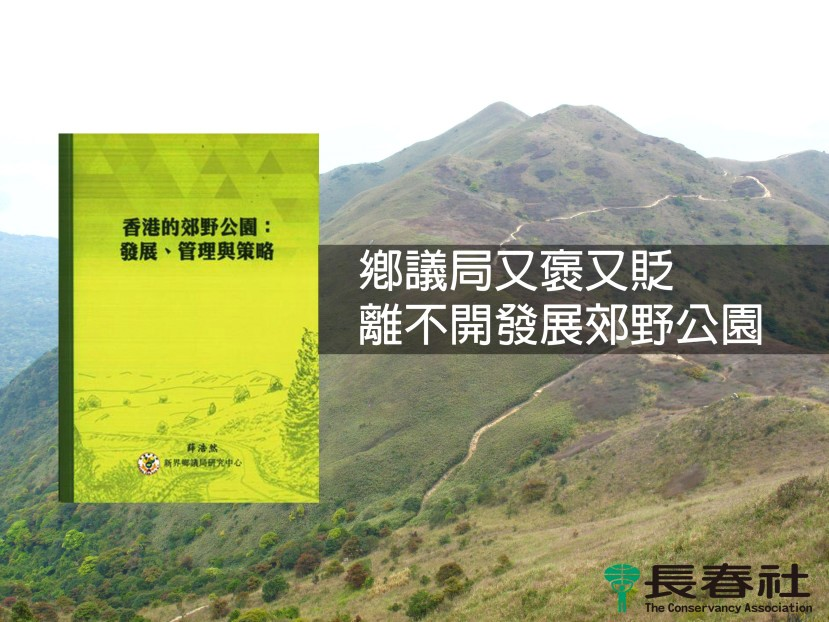
當特首以至「智囊」們每隔數月就在開發郊野公園一事上出口術,留意到年中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相對低調地出版了一本名為《香港的郊野公園﹕發展、管理與策略》的研究報告(下稱《報告》),《報告》的結論縱未必把「發展郊野公園」放在當眼處,卻嘗試從多方面「釐清」康樂價值在規劃郊野公園中的角色,間接亦為開發郊野公園論推波助瀾。
一褒:郊野公園「重康樂無保育」?
作者從回顧《戴爾斯報告書》,以及麥理浩主政時設立郊野公園的過程,認為郊野公園起初建立的原因,「是為市民提供符合市民需要的康樂和旅遊空間,而非當前部分爭取環保人士所聲稱的環境保育」,又指「不應本末倒置,硬將發揮郊野公園的康樂旅遊功能過程中所必需的維護環節當作是設立郊野公園的根本目的」。
不過,將整段郊野公園成立的背景定調為「重康樂無保育」,淡化發展郊野公園的保育角色時,以下這些事件都一一被略過﹕回顧戰後的林務工作史,政府因需取得柴薪、保護集水區、防止水土流失等目的而廣泛植林時,林務官戴禮(P.A. Daley)在《林務及其在香港自然資源保育工作的地位》(Forestry and its Place in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in Hong Kong)中,已強調林務在保護自然環境中可發揮的重要作用﹔《戴爾斯報告書》中,建議的幾個保留地區表明是兼顧生態學研究、動植物保護、防火等遊樂以外的目標,亦認為鄉村就風景及歷史之觀點而言,須加以保留﹔由港督戴麟趾委任的「郊區的運用和保存臨時委員會」,當時發表了《郊野與大眾》(The Countryside and the People)的報告,除了康樂,也有加強在已侵蝕土地上重新植樹、成立更嚴謹的自然保育區等保育建議……
你固然可歸納出如前漁農署署長王福義教授在八十年代的研究所指,早年提倡保育的聲音,主要是來自在專業、學術研究的人士而非普羅市民,然而,這些與保育相關的大事從郊野公園發展脈絡來看,理應是相互支持的,並經過累積,成就郊野公園的建立。近年,植林作用擴大為綠化郊野,著重採用本地樹種,提高郊野公園的生物多樣性,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郊野公園界線,怎會與保育、科學拉不上關係?
一貶:香港人康樂模式已變?
作者薛浩然根據漁護署的統計數字,指郊野公園的訪客人數,由2009年1,360萬人次,下降至2013年的1,270萬人次,四年內下跌6.6%,作者把原因歸咎於「市民康樂旅遊模式出現了根本性改變」。1965年由戴爾博夫婦撰寫的《香港保存自然景物問題簡要報告及建議》(Conservation of Hong Kong Countryside)(又稱《戴爾斯報告書》)中,提倡建立類似郊野公園的概念,因為當時「僱員負擔不起去日本、菲律賓旅行」,認為香港需有廉宜的渡假設備,惟作者指今日香港人收入已提高不少,《戴爾斯報告書》所指的「負擔不起外遊」現象已幾乎不存在。
當一班「智囊」要求公眾以科學、理性的角度去理解郊野公園的存廢時,他們同時卻不懂以同樣的角度看待一些數字,2015年過去三季的郊野公園訪客數字為8,249,000人,比去年6,644,000人高出兩成四,郊野公園,的確有人用的。香港人的康樂模式或許出現了改變,但負擔得起去外遊的香港人,不一定會放棄到城門水塘行一轉、到大棠賞紅葉、去大東山影芒草、去北潭涌燒雞翼。
這類針對「郊野公園少人用」、「香港人康樂旅遊模式改變」而去支持發展郊野公園的一方,本身亦逃避如何改善郊野公園的管理,提升郊野公園的康樂價值。2012年漁護署進行過郊野公園遊客滿意度的意見調查,2013年審計署亦就郊野公園的教育活動、宣傳推廣等問題提出過改善措施,他們為何不曾去問﹕到底這些建議如何改善郊野公園,還有更多可以做嗎?為何要直接判郊野公園死罪,非發展郊野公園不可?
《報告》對「康樂」二字的一褒一貶與現實合流,就是依然有人建議「返內地減壓」,不擔心發展郊野公園後香港人壓力無處宣洩﹔依然有人不斷數臭郊野公園的界線一直不客觀、不科學,質疑郊野公園是否「一吋都不能碰」。然而面對狙擊,近來公眾或響應環團呼籲,走一趟郊野公園打卡,或自發聯群結隊,走到郊野公園執垃圾,這叫教育活動的同時,我相信無形間也是民間對「有壓力就要去外國散下心」、「保育就係咩都唔郁」的有力回應,這一點一滴,將不致讓公眾在「房屋大過天」的氣氛牽著鼻子走。
長春社助理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
刊於2015年12月28日立場新聞及香港獨立媒體,12月29日主場新聞博客群

